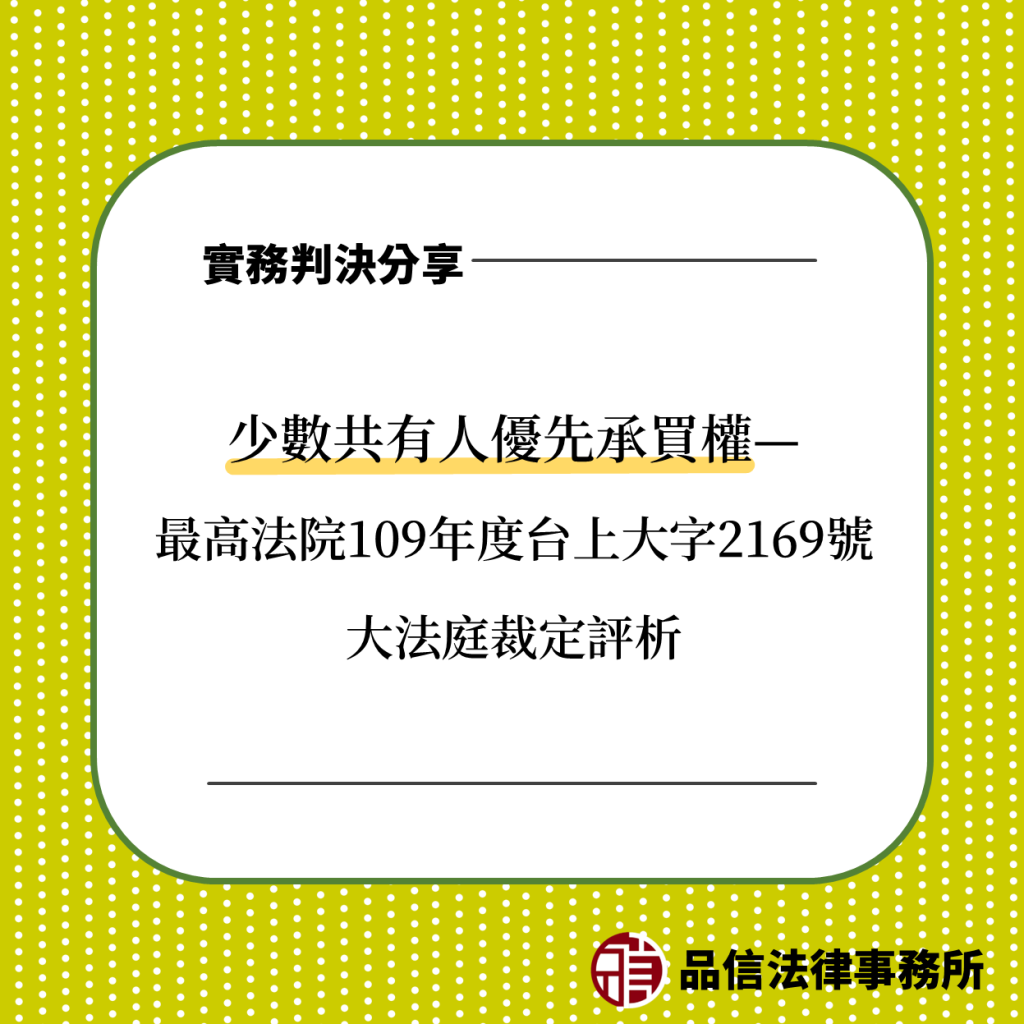一、問題意識
(一)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優先承買權究為債權效力抑或物權效力?
(二)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優先承買權究為形成權抑或請求權?
(三)土地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出賣共有之土地,未依同條第2項規定通知他共有人,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他共有人於移轉登記後知悉上情,得否依給付不能之法律關係,請求出賣土地之共有人賠償損害?
二、大法庭裁定主文
土地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出賣共有之土地,未依同條第2項規定通知他共有人,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他共有人於移轉登記後知悉上情,不得依給付不能之法律關係,請求出賣土地之共有人賠償損害。
三、裁定理由摘要
(一)優先承買權僅具債權性質
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並未如同法第104條第2項後段設有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之明文,故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之優先承購權僅具債權效力。優先承購權人於他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予第三人時,固得行使優先承購權而與該共有人訂立同樣條件之買賣契約,然倘該共有人本於其與第三人之買賣契約而將出售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優先承購權人不得主張該買賣為無效而塗銷其移轉登記。
(二)優先承買權屬於共有人所得行使之請求權,而全部共有物處分後,少數共有人已失去共有人身分,故不得行使優先承買權,亦不得主張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規定,旨在防止共有土地或建物之細分,以簡化或消除共有關係,減少土地使用增加之成本,俾利共有土地或建物之管理與利用,行使優先承購權之人及對象限於共有人。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出賣共有土地全部,並已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共有關係於標的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後消滅,原共有人亦均喪失共有人身分。縱為出售、處分者違反通知義務,然未受通知者於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後,已無從再行使共有人優先承購權,且為出售、處分者亦無與之訂立買賣契約之意願,渠等間自未成立買賣契約,該未受通知者即不得依給付不能之法律關係請求出賣之共有人賠償損害。
(三)少數共有人得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出賣之共有人違反通知義務,致未受通知之他共有人無從行使優先承購權,倘構成侵權行為致該共有人因此受有損害,自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則請求出賣之共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判決評析
(一)本件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見解認為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共有人優先承買權之性質僅具債權性質,而不影響共有物處分之效力,此部分與過往通說見解皆相同。惟仍與過往通說見解有所不同,過往通說見解認為優先承買權性質屬於形成權,一經行使便與相對人間成立買賣契約,相對人如不履約則應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至於本件大法庭裁定見解則認為優先承買權屬於請求權而非形成權,且相對人如無締約之意願,則買賣契約並未成立,故少數共有人不得主張給付不能損害賠償,僅得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除此之外,大法庭裁定見解更認為於土地移轉登記後,共有關係消滅,已無從再行使優先承買權,限縮了優先承買權之行使期間。
(二)對此一大法庭裁定,學說批評並表示,相比形成權說,採取請求權說只是徒增權利人之勞力、時間、費用,有害公益層面訴訟經濟,形成權說更有助於優先承買權之立法目的實現(顏佑紘,論優先承買權人對移轉應有部分與原買受人之共有人得否依契約責任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評最高法院 109 年台上大字第 2169 號民事裁定,台灣法律人,第 3 期,117-140 頁,2021年09月。)
(三)又學說見解認為,優先承買權之發生時點於多數共有人出賣共有物時即已發生,且得行使。行使時,權利人是否仍有共有人身分,在所不問。即使多數共有人已辦畢移轉登記於原買受人,此僅導致優先承買權「無法滿足實現」(蓋於債權效力說下優先承買權不得對抗原買受人),不因權利人喪失共有人身分而消滅、不能行使,大法庭裁定乃混淆了「權利是否存在而得行使」與「權利是否滿足實現」兩者之意涵。(陳忠五,多數共有人未通知少數共有人行使優先承買權而處分共有土地的契約責任-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大字第 2169 號裁定簡析,台灣法律人,第 4 期,159-167 頁,2021年10月。)
(四)此外,大法庭裁定雖謂少數共有人得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惟在優先承買權僅具債權效力之前提下,是否能滿足侵權行為之責任要件,仍有待實務見解之發展。
【本文感謝林亞駿協助整理】